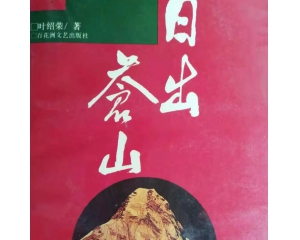|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对话系列之释定融 丧失帮助别人的能力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接受别人帮助的能力。我是个出家人,出家人和在家人对灾难的认识还是不同,大家觉得尘肺病患者是需要帮助的群体,而我作为一个佛教徒,并不认为是我在帮他,相反,是他们在成就我的慈悲心。 ——《声音——尘肺之殇》导演释定融
因肺组织纤维化及肺气肿、气胸压迫心脏,陈久红睡觉的姿势代表了所有尘肺病患者的姿势。
今年8月22日陈久红离世,年仅36岁,留下12岁幼子和70多岁的父亲为他守灵。
释定融 原名杨霁,沈阳人,当过兵做过警察,6年前剃度;用9个月时间行程6万多公里在8个省区拍摄尘肺病群体 首届阳光华语纪录片奖的一部入围影片《声音——尘肺之殇》,最近引起关注。纪录片的拍摄者历时9个月,行程6万多公里,到达8个省区,镜头对准“矿难中的矿难”——尘肺病人群。 在西南大山里,在川西平原少数民族地区,尘肺病正吞噬着一个个年轻农民的生命。他们对尘肺病一无所知,他们靠诚实的劳动谋生,等待他们的却是残酷的命运——仅在江西修水县上杉乡,已有80多人死亡,500多人等待死亡,这里几乎成了一个寡妇乡。 “(关注)尘肺病患者的生存状态,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刻了。”《声音——尘肺之殇》导演释定融反复说。作为尘肺病救助志愿者,他希望通过纪录片让社会更加关注这个弱势群体。 释定融,6年前剃度,“半路出家”,原名杨霁,老家辽宁沈阳,当过兵做过警察,经营过广告公司,虽是佛门之人却最看不破红尘,“我从来不觉得出家人的生活就应该是闭门修行。” 好多人还以为是艾滋病 东方早报:怎么会想到关注尘肺病人? 释定融:最早关于尘肺病的记忆是我的一个邻居,他常常呼吸困难,沈阳的冬天又特别的冷,他总是抱着暖气,而到了夏天,也只能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基本上不怎么走动。直到2010年12月,我到了北京,和曾经采访过我的记者王克勤见了一次面。当时王克勤正发起对甘肃古浪尘肺病患者的救援。 通过他的讲述我才知道,尘肺病不单是受害者个人受病痛的事儿,而是(病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散落在农村各处,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农田抛荒,患者家庭破碎、子女辍学打工等等。谈话之后,我当即买了一张火车票,直奔兰州。了解了一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后,我与牵头的志愿者火兴才取得了联系,进入古浪。从此以后,尘肺病患者的病况和他们悲惨的生活都被我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东方早报:片头74个尘肺病患者的声音不绝于耳,令人震撼,据你所知全国目前尘肺病患者的数量大概有多少人? 释定融:目前,根据原《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和记者火兴才在前期调查的数字,还借鉴了官方公开公布的数字,保守地说有100万以上。 就我自己走到的地区,尘肺病患分布在包括内蒙古、辽宁、四川、江西、甘肃等偏远山区。比如甘洛县,它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地理环境上看,这些边远村落几乎都在海拔1200米到1600米的高山上,十几年间,青壮劳力基本都在矿山上打过工。这些地方,保守估计,患者应该在3万人以上,潜在的也可能有3万人左右。 它潜在的原因是,像彝族自治州地区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凉山州疾控中心掌握的情况告诉我们,整个自治州艾滋病和毒品泛滥。在矿上打过工的农民工,待尘肺病并发症像吐血等症状出现后,很难判断自己得了什么病。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当地人认为艾滋病是很邪恶的病,对于这种邪恶的病,病人死后就被放在较大的河床上直接焚烧,骨灰也就随着河水冲走。所以很多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尘肺病晚期了,很快就走掉了。 被救助对象问是不是骗子 东方早报:四川省甘洛县是尘肺病死亡率最高的农村地区,现今村里大部分都只剩下老人,这些老人未来怎么生活? 释定融:没错,尘肺病的发病是很快的。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也许就有有两个重伤病人死去了……从7月31日到现在,新增死亡人数就在10例。 甘洛县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是基层政府,能力也有限,实际上给当地尘肺病和患者家属解决的也是杯水车薪。如果青壮劳力都没有了,可想而知老人的生活状况是很悲惨的。比如我们接触到的尘肺病患者郭来强的家庭:75岁的老母亲32岁就守寡,她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郭来刚,老二郭来强,老三还是个残疾人。老大郭来刚是我曾经在沈阳军区的一个战友,他在部队上还立过战功,但他已经去世了。老二郭来强现在已经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现在老母亲就靠种别人的两亩地来维持生计,还要养活孙子,这种凄惨的生活状态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东方早报:在你拍摄过程中还看到什么更严重的问题? 释定融:江西修水县上杉乡,五百多人都姓朱,是南宋朱熹的后裔。1985年的时候,上杉土龙山这里发现了锌矿,结果朱熹的后代全体都在挖锌矿。统统得了尘肺病,你说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还有一个姓吴的人家,一共有三个儿子,全都死于尘肺病,一年死了两个,间隔不到两个月;在纪录片里有一个叫朱金龙的,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得了尘肺病。他们家有二百亩水田就撂荒在那里。在上杉乡,这种农田撂荒现象非常普遍,情况很严重! 今年3月份,我到上杉乡的时候,并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去调查,因为乡里边干扰也很厉害。但据我粗浅的了解,撂荒水田大概不低于1000亩。因为每年还是要种地,他们就把水田改成了桑树田,养蚕。你要知道,水田改成桑田,就没办法再改成水田了。这是极其恐怖的事儿。还有尘肺病患者朱福春的一家,他女儿朱晓娟,不到15岁,父亲死后,她只能跑到东莞那种血汗工厂去打工。朱福春的儿子朱林根在广东富士康的企业打工,那天他站在富士康工厂外的一个天桥上对我说,如果他的母亲再出问题,他就肯定活不下去了。听得人真是很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