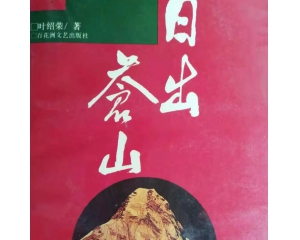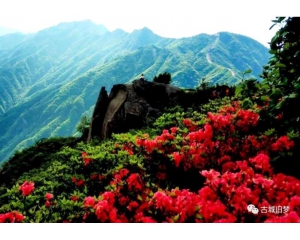|
刘戈: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把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今日观察》评论员) 钱是一方面问题,现在中央政府要用大量资金,包括土地出让金的10%用来投入水利建设,那么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机制来让这个钱用在刀刃上,而且除了建设以外,今后还有维护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粮食价格比较低,而且很多农田只能种粮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很便宜,农民就没有积极性。尤其是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是50、60、70岁以上的老人在种。旱灾也好,涝灾也好,哪怕颗粒无收,损失有多大?现在一个农民工,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在外面干一天活至少挣一百块钱,三天就可以把净利润赚回来,那么积极性何在?即使国家投钱,要是农民没有积极性,怎么样贯彻下去也是一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除了水的建设以外,这个水在运营过程当中,分水到谁家的这个矛盾是经常会出现的。公共池塘悲剧,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损失俱损失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干。有村里的青壮年提出要求的,就是多少钱干这个事情,但村里又没有这个钱,所以大家最后都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地全被冲掉。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把钱落实;另一方面,在农村里把原来的一些可用的机制,比如把基层的水利管理部门建立起来,让水的分配,水的运营机制通过价格的调整,到最后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运营,自我完善的体系。 李国祥:通过多渠道的探索来逐步缓解农村水利投资主体缺乏、资金不足的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财政预算,根据国家的财力适当增加水利建设的比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通过土地出让收益补充资金来源。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培育农村水利建设的管护主体,通过他们,将来可以通过水费的收入形式,通过银行进行贷款,通过多渠道的探索来逐步缓解农村水利投资主体缺乏、资金不足的难题。 林万龙:关键是加强农户的投入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加强农户的投入:第一,就是对于一些个人收益比较明显的设施,我们可以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调动农户投入的积极性,把我们原来的公共服务转化成一种私人提供,就是农户自己投资,自己收益。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应该有效的把政府的投入和农户的投入结合起来,考虑到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是由政府投资的,但是这个资金的具体使用可以由一个村,或者若干农户具体使用这笔资金。 刘戈:关键是政策资金如何落到实处 (《今日观察》评论员) 南方有个谚语:“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很多农民说,我们现在不靠种粮食吃饭,他从内心里已经离开了土地,但是他在农村的地又属于他。在这样两难的状态下,政策资金如何落到实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文件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复杂性的设计,所以这方面还要细化它的复杂性。 郑风田:要解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出现的合成谬误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现在,农田水利建设出现了一个合成谬误,农民都不种地了,国家粮食安全就会出问题。中央已经把水利建设落实了,拿出土地出让收益的10%,但是这有一个矛盾,我们产粮食地区的土地没有收益,因为土地在县里,没有收益,就没法拿出土地赚钱。土地收益特别高的大都市,它的农地特别少,基本不种粮食。所以我强烈建议国家一定要把土地出让收益统筹起来,应该中央统筹,投入到我们粮食安全最需要的地方,投到那些穷的地方,彻底把农田水利建设做起来。水利部长算了一个数,我国每年的农田水利土地出让金大概是2.9个亿,再把其他各种各样的成本刨掉,真正每年能有六七百亿投入到基层政府的农村里,再加上中央的惠农资金,加大投入。还有机制上,因为大户承包有时容易带来整体小弱农户受损,所以可以通过用水者协会,通过机制保证,这样彻底保证我们的饭碗和我们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