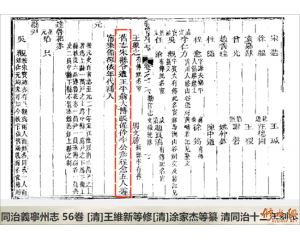|
(一) 一九九二年深秋,田地里忙完后,父亲又盘算着要去山里了。 “还差五十来丈椽皮。”在昏黄的灯下,父亲的眼睛发着光,他连吸了几口烟,将自己用细竹蔸做的烟斗在椅子脚上敲得山响。母亲在铡猪草,停下来,叹口气:“要尽快,趁天好,山路难走。”她说完,又咔嚓咔嚓地不停;灯火摇曳昏暗,猫在门角里踡成一团。 我知道,父母这五、六年来都在谋划着起几间房子的事。老屋实在破了,临东边的外墙被雨洗得不成样子,好几个地方都穿洞了,风一吹都感觉得到在晃;又挤得不行,八家人住一起,我家一间正房、两间偏房、一个过厅;父母与弟、妹睡在正房里,我毕业后在过厅里搭个木板铺睡。过厅与猪圈鸡圈只隔一堵墙,牲畜们有时半夜叫闹起来,叫人恼火得很。因此,能做几间新瓦房,就成了我们全家最大的愿望了。 我九零年师范毕业分配在沙坪完小教书,学校设在破旧的杨家祠堂,离家差不多二十里路,一般都住校的,星期一早上去,星期六上午上完课才回家。两年来,清贫而单调的生活一点点击溃我的意志,我以为教书是最无奈的选择,终究有一天,我会离开三尺讲台。 “知足吧!教书多好,不得罪人,朝朝代代都重视的。”父亲每每这样劝我,又说:“生活难哪,有谁容易啊?”我不以为然,以为天下路多,自己可以选一条宽些直些的去走。经历几次诉求无果的折腾后,心劲儿有点低落。 内容来自xiushui.Net “林伢,明天进山去不?”父亲的问话生生将我从茫然空想中拽出来。“去、去吧?”我没有一丝准备,放下了手中的笔,一节备课只写了一半。母亲停止铡猪草,断然说,“你不行,恰不消的”。 “我担得起的!”声音大得吓了自己一跳,“我都二十岁了,担得起的!”自认为个子比父亲高一头,力气比瘦小的父亲要大,他能做的体力活,哪会难得倒我?父亲是读了一些书的,只是因为祖父成份不好,不能往上升学。后来去修柘林水库时,做过卫生员,算半个赤脚医生;又在村里的小学教过几年书,算半个民办教师;可干农活不在行,大集体时记工分比别人要少。 “我没去过山里,想去看下。”这倒是我真实的想法。父亲在农闲时,会同人一起进山里掮树担板子,以前是贩卖给通城人,赚几个钱用;近几年是筹备做新房子用。父亲常是半夜才回来,往往能带回一些梨呀枣呀栗子呀什么的,我和弟弟妹妹各分一份,能吃几天。在我的印象里,山里是美的,是丰饶的,山里人不愁吃,有福气。 “早点睏吧,路难走的”。父亲将烟斗放进裤兜,拍拍手去睡了。母亲叹了几口气,帮我打了洗脚水来。 我很期待,明天能进山里看到不一样的生活。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二) 父亲左肩向右斜扛一根红光锃亮的竹扁担,扁担后头系着几根棕索,前头吊着一个尼龙袋,里面是两碗白米饭,饭上盖块肥肉,杂拌着一些炒干酸菜与萝卜。他左手抓着尼龙袋的口子,右手拉着棕索,稳稳地走在前头。天还漆黑,远处一只狗先慢后快先轻后重地叫了几声,近处的狗们逐渐响应起来,汪汪汪汪的声音在霜风里撞击着,像是在比谁嗓门大。 “瘟狗”。父亲轻轻地骂一句。我紧跟在后头,左手提着一根扁担,右手晃着个手电筒。手电光极不老实,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将夜色划得破破烂烂。扁担也不安分,一下子拄在地上,一下子扫在山道边的树杈上,乒乒乓乓响。 “悠着点”。父亲说,“现在还没到三仙岭,还要经蛇下源过路口乡,从仙桥到古市南山过河,由汪坪进东山,沿东山上到牛岭,上山还有十多里”。 我收敛了些,心里却不以为然,自认为走几十里路是不怕的。天色渐渐亮了些,近处的山、树、屋都凸现出轮廓来。爬上一道陡坡,一阵风扑过来,父亲抖了一下。我眼前一片空阔,几点波光闪动着,父亲告诉我到了石达水库。 “春上那次,下屋美黄掮树回来在堤上歇伙,去脚下洗手,一头栽水里了”。父亲指指前头,“大伙拼死拼活抢了他上来,命大”。我的心陡然紧缩起来,原来就听老人讲古,说这水库有簸箕大的脚鱼,能上岸将落单的行人拖下水。这水库里每年要浸死几个人,是冤死鬼找八字相合的当替身。我感觉一阵寒气从裤管里往上窜,在渐渐淡去的夜色里,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刷刷的脚步声也格外清晰。 内容来自xiushui.Net 当天放亮时,我们到了仙桥。从半山腰远远见一片村舍,随意散落在山脚下;一条小河蜿蜒曲折,一架木板桥上有人挑着水在走;淡蓝色的炊烟从那些黑瓦的缝隙里蒸腾起来,路边树杈上的白霜发着光。 “到南山樟树坪里要歇一下”。父亲微微喘着气,依旧稳稳走在前头。我隐隐觉得脚板有点酸,想歇一歇,又不好意思先开口,觉得父亲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不再七想八想,闷在后头跟着。 (三) 这是一群古老的樟树,肃穆地驻守在南山的河滩里。父亲坐在最大的那棵樟树下的石头上,抽着烟,烟圈在树的枝丫间飞旋。我在树间徜徉,嗅着从枝叶散发出的清香,树干都高高大大,怕要三人才能合抱过夹;枝丫繁茂,深秋早晨的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射进来,照着地上几簇枯灰的灌木;在河边的那棵最高的树的顶上,有一个用细小枯枝搭的乌鸦窝。 “林伢,莫再往前去了。”父亲见我靠近了那棵唯一的木子树下那个社庙,急忙喊道。我悻悻然折回来,坐在他旁边的小石头上。父亲说,这社庙里土地公公脾气不太好,不能冒犯。两年前,竹埚垅一伙人掮树经过这里,有个年轻人在社庙旁屙了尿,回家后小便肿得手臂般粗。后来请了“马脚”,专门到社庙前烧了十斤三两“表心纸”和一百零三个“金银锭",才消了肿。我有点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兴许是被什么毒虫子咬了吧?抑或是什么东西过敏?不过,还是暗自庆幸刚才忍住没在那附近小便。 修水网 一个驮背的老人,牵着一头懒洋洋的牛过来。“叔,这木桥几时垮的?”父亲站起来,笑着问道。 “早垮了。八月间一场大水,少见的事哦。”老人在牛屁股上拍一鞭子,淡淡回答。“如今水不深,可以过。”他走过去十来米,扭过头笑笑补充。 “谢谢!”父亲扬扬手,眯着眼睛,像是被一道漏进的光射中。然后,利索地脱去鞋袜,将裤管挽至大腿根下,向河边走下去。“林伢,你等下,我去试试水。”他边说边下了水,明显看他一个啰嗦,马上又缓过劲往前淌,水浅处只到脚踝,水深处快浸到膝盖了。他过到对岸,放下扁担与尼龙袋就准备折回来。 “我驮你过来。”父亲在那边挥着手,喊声被流水的声音冲淡不少。 “不!”我猛然回过神,赶紧脱掉鞋袜下河,冰凉的水让人想尿尿。父亲僵在水里,指着河中央水急的地方喊:“得注意脚下,慢一点,侧着身子,石头滑,把裤子挽高一点,水深的地方用扁担撑一下。”我忍住尿意,一步一步挪过深水处,在透明的水底,石缝里有“黄丫角”在钻来钻去。 过了河,沿着河堤到了汪坪。又走了五、六里,才绕过东山到牛岭脚下。 本文来自修水网 “歇一下吧!把鞋带系紧一点。”在岭脚的大松树下,父亲停下来,又扭头指着远处那一片人家,有点向往地说:“那是东山大屋,出过大人物的,清朝光绪年间傅康衢中了举人,据说傅氏后代还珍藏着一块皇帝赐的金匾呢。”我逆着深秋上午九点钟的阳光,只看见屋场里老人安静地坐着,小孩在追逐游戏,村道上有人用独轮车运石头,有人扛着树木急走,还有杂货郎在慢悠悠地摇着拨浪鼓…… (四) “牛岭十八里,三十六道弯"。山路陡峭曲折,路面凹凸不平,行走其间,没有一股子牛劲是不行的。 父亲将夹袄脱了,挟在左腋下,汗水将旧棉布背心洇湿了,黑黝的肩膀及脖颈泛着油亮的光。每转一个山头,父亲都放慢脚步,好让我跟上。 初上岭时,我还能紧跟父亲的步子。有几次,远远看见前面山头有一棵大树或者一块大石头,我还跑着抢在他前头,靠一靠树干摸一摸石头。渐渐地腿肚子酸酸的,汗珠子在额头上滚下来,有一滴滑到眼睛里,赶紧用手背去擦;过不了几秒钟,又一滴滑进去,辣得连眼皮都睁不开,不得不停下脚步来。 “上山的徒弟,下山的师傅。”父亲说:“走远路、爬山路要长情,气劲足时不能冲冲蹦蹦。现在上山空着手,还算好走的;下午下山要担着椽皮,更难走,脚下更要准头啊。”我靠在路中间一块麻石上喘着气,一阵风吹过来,浑身爽快。对面半山腰的一团云正慢慢向我划过来,“咣当咣当”砍树声伴着不成调的歌声从某个山洼传来,偶尔有人掮着树木或挑着柴像牛一样喘着气从山上下来。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到对面山坳里老傅家喝口水。”父亲指着前面,叹口气说:“也是个苦命人,十几年前死了老伴,前年相依为命的儿子在‘挂壁崖’采草药摔死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竟有点喘不过气来;顺着父亲指的方向,隐隐看见一角土屋怯生生地探出头来。 山里的人家,看起来不远,走起来费力。到了山坳里,向左拐个弯,上一道短坡,再爬上几级麻石台阶,有三间土房子。土筑的墙体有几处裂开了,屋顶上盖着树皮与草,窗子上一张破油布在随风飘摇。房子前是一个不大的空场,几根没剥皮的杉树随意地躺在地上,几只鸡正用脚爪在土里刨着什么,见有人来,訇地一声跑了;在大门前的左边,放着个水缸,一根竹子悬在水缸上头,一股清清亮亮的水从竹子里泻出来,叮咚叮咚滴到缸里。 “老傅,老傅!”父亲在大门口,冲着里面喊。见没有人应答,父亲从左裤袋里摸出一个油纸包放在大门里一张脏兮兮的桌子上,里面是些黄烟丝。这是他自己种的烟叶,荫干后切成丝,拌上一点菜油,很香的。“老傅喜欢抽我的烟。怎么不在家呢?是上山去了吧?”父亲自言自语,笑一笑摇摇头,从土墙上摘下一个勺子,递给我说:“喝口水,别急火,莫呛着。歇一下,再上两道山梁到童家屋里买椽皮。”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五) 童家屋场在一个山台子上,眼底下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几片棉絮状的云戴在几个山尖上,仿佛是娇美少女发髻上的百合;一只老鹰在山谷里滑翔,突然又坠落在对面石崖上去了;在屋场后面的高山上,一沟水哗哗地泻下来,在右边的石池子里打着旋,又从青石板盖着的沟渠里倾注下去。屋场横斜着十几户人家,都是黄土墙,有几堵墙上还用白灰刷了一块,上面用红漆写着“毛主席语录”,字迹有些斑驳了;家家檐下吊根竹竿,晾些颜色单调的衣裳;还有好几堵墙上钉满了竹钉,竹钉上挂着成扎的芝麻秆或者红薯藤。 “黄家嫂,在家不?”父亲在一户人家大门口停下,一边挥着扁担,吓退了一只蠢蠢欲动的黑狗,一边冲着屋里喊。 “哎,在咧。”话音刚落,一个利索的中年女人从屋里出来,左手提着木桶,右手遮在眼皮上头,一张还算清秀的黄脸从暗黑的门洞里凸出来。 “老周哦,有个多月没上岭了吧?快进来坐。”女人赶紧放下木桶,挪过两个凳杌,对着凳面吹了吹气。“莫客气。”父亲笑一笑,指着我说:“这就是我大崽,在教书的,今天是星期天,学堂不上课。” “好后生家啊。”黄家嫂将我从头到脚看一遍,拍了拍围裙说:“吃国家粮的,好哇。你也吃得这个苦么?”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不怕的。”我笑着回答,坐下来偷偷地揉了揉酸软的腿肚子。屋子里很简陋,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从女主人与父亲的攀谈中,我知道了她一家的大致情况。 童家屋场十四户人家,只她家姓黄。男主人黄良禄当年修东津水库时与父亲很识性,也是个极勤快的人,一年到头在山上忙活:侍弄几亩薄地,采草药砍柴卖,猎兔子打野猪,帮人拉锯锯板子……。他们生了四个女儿,五年前才躲在县城亲戚家生了个儿子;大女儿嫁在南山,二女儿与东山卖肉的傅红鼻子的独生子订了婚,三女儿辍学了,细女儿在镇上读初中,小男娃在家玩泥巴与猫。 当天中午,我们在黄家嫂子家吃饭;女主人将我与父亲带的冷饭菜蒸热,另外为我们炒了个兔子肉。当父亲看到主家铁炉罐里的几乎无米的黑薯丝饭后,毅然将我们的饭倒进去搅和一阵子,那颜色变灰变白一些了。 父亲与黄良禄喝了两小杯自家用红薯酿的酒,黄叔指着我,打几个嗝对桌上吞咽着的细女儿说:“要努力读哦,像你哥这样吃上国家粮就好了,祖宗菩萨保佑啊”。“嗯,哈,他倒不安心啰。”父亲嘿嘿几声,脸上红晕了一块说:“细姑俚有文气,会有大出息”。黄叔放下筷子,楞楞地盯着我说:“自古以来,教书就是好。天地君亲师,被人敬着呢!我细姑俚能当个老师,怕要祖坟上冒青烟。”风从门洞里捅进来,我的眼睛被刺得痒痒的,用手一擦,湿了一手背。 内容来自xiushui.Net (六) 吃过午饭,黄叔带着我们到屋场最东头童国兴家买椽皮。 “一公分厚的五角一丈,一点二公分厚的六角一丈”。童国兴是个光头,正午的阳光在他头皮上跳舞,此刻,他两手各掂一段杉树椽子向父亲摇一摇,说:“干透了,锯得方方正正的,超值的。要多少丈呢?” “又涨了。”父亲显得有点懊恼,“前天有人在画坪买还是四角一丈呢。” “嚇!莫开玩笑了。”童国兴斜着眼扫了父亲一下,“我大舅哥是画坪晏家的,昨天还邀我再涨一点。不然,刨去人工费伙食费,赚个屁哟。诚意要买,一公分厚的四角八,一点二的五角八,不能少了。看你也是老顾客,不能再少了。” “贵了。”父亲拍了拍脑门,点上烟斗吸了几口,接着说:“春上还只有四角二。你老板只管涨,谁买得起。”我呆在一旁,看他们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心里陡然生出一股苦涩的滋味来。 约摸过了半个钟头,经过黄叔撮合做中,父亲买了三十丈一点二公分厚的,二十六丈一公分厚的,统算五角二分一丈。父亲将一沓钱数了两遍,往前一伸,童国兴接过去,细细再数一遍,又数一遍,断然说:“不行,不行,只二十八,差一块多。不行,真不行的。”父亲再从裤兜里摸出皱巴巴的伍角来,拍到童国兴手里:“童老板,再没有了,荷包空了,要韬光了!”边说还把裤兜都翻出来给他看。 xiushui.Net “哎!赚不到钱哦。算了算了,快去绑好!”童国兴扬一扬手说。 父亲与黄叔便开始绑椽皮了,我在一旁打下手,将散落杂乱的收拾整齐来。他们先绑三十丈厚的椽皮,首先左一块右一块将一端错叠起来,用棕索交叉缚紧;再把另一端分开,将竹扁担插进中间位置,调整重心后,用较粗的粽索把扁担固定好;最后用两段绳子把左右两端捆紧。父亲用双手扶起来,又扛在肩上闪了闪,觉得满意了,就将A字形椽皮担子靠墙放下。 正要着手绑另一担时,“咣咚”一声巨响,只见一根大杉树向我们这边滚过来,在约一米远的地方,被几截断砖头阻着了。 “秀才,你哑了,吓死人。”童国兴指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汉子骂道。“对不起,太重了,放下时没把住。”那人只尴尬地笑着,左手揉着肩膀,右手用块旧毛巾擦脸,衣服全汗湿了,发鬓上的汗珠在阳光下亮闪闪的。 “秀才啊,这个是正式老师,我侄子。”黄叔指着我说。“哦?”秀才有点愕然,我笑了笑,伸手握住了那一双伸过来的粗糙的手。 父亲他们继续绑着椽皮,我与秀才在一旁聊了起来。秀才其实名叫童有财,是牛岭埂上教学点的代课老师。“背时哟,我八零年下半年来教书,上面规定八零年上半年以前才算正式民办教师,才发民师证。”童有才擦了擦脸,苦笑着继续说:“我连民师都不算,没资格参与转正及师范考试的。点上二十二个学生,三个年级,只有我与我老婆两人教,忙得连轴转哦!” 内容来自xiushui.Net “你们两夫妇教三个年级?待遇还行不?”我问。“两人半年五百块。”童有财叹口气,望着对面山谷里,有点迷茫说:“原来分过一个正式老师的,去年托关系转调镇上中学去了。上面一时没人,村书记叫我老婆来了。她只有初中毕业,上些音乐美术,搞下卫生伙食。有些学生家里远,中午在学校吃的。” “是亏了你们哦!”我在沙坪小学教三年级语文,另加几节美术、体育课,每周十六节,比童有财要轻松多了,工资也要高一些,还老怨天怨地的,不应该呀! “小周,你命好哇!”童有财一边脱下左脚上烂了两个洞的解放鞋,抖落出里面的沙土,一边说:“你们正式老师好哇,吃国家粮,工资比我们高一倍。不过,你们水平也高,伢崽还是更喜欢你们教的!” 山谷里的风再一次吹乱了我的鬓发,也吹皱了我的原本以为没有波澜的心湖。 (七) 晌午过后的太阳有点羞答答的,刚从一团云里露出半边俏脸,又躲到对面顶峰的后面去了。父亲挑着三十丈厚椽皮走在前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时不时要侧身避让山路旁的枝枝蔓蔓;碰到路中间有石头或者要拐弯下坎时,他一定要警示着我注意脚下,都是先伸左脚试探着踩稳,再迈开右腿。我挑着二十六丈薄的跟在后头,担子不重,就是总会磕到土坎上,或者被枝蔓钩住。父亲在前头走得不紧不慢,我好几次要想超到前面去,他不让,便只好巴在后头。 xiushui.Net 经过山坳老傅家时,右边短坡上一个干瘦的老人背着竹篓吃力往上走。父亲停下脚步,朝老人挥了挥手,张张嘴却没喊出来,终于只是叹息一声,讷讷然说“老傅真老了!”老人没有发现我们,而我们也宛如两只负伤的甲壳虫,缓慢而笨拙地爬行在羊肠似的山道上。 渐渐地,我有点跟不上父亲的步子了。他被汗水洇湿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那略显粗重的喘息声也消散在秋虫的碎语中。我时不时地将担子在两肩上交换,颈后面的肉有点麻辣辣的,腿肚子一股酸劲往小腹上挤来;可恼的荆棘枝蔓,总是突然地牵扯一下我的担子,使得我踉踉跄跄,一如喝醉的酒鬼。 “歇一下吧!"快到岭脚下时,父亲将担子靠在右边山坎上,边说边用手抹一抹脸往地下一摔,一串汗珠打在脚下的尘土里。我啪地将担子摔倒在坎上,往地上一下瘫坐下去,嘴里扯风箱似的喘着气。 “莫坐在地上哦,容易累的。路还长着呢!”父亲用右肩顶着担子,豆大的汗珠在黑瘦的脸上乱爬;他不停地边抹边摔,气息匀些后,又抽了两杆黄烟。 我有些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听父亲继续说:“山里人就是有柴烧,暂时还有树卖,生活还是比塅下苦。山上极少水田,稻米金贵;土地又薄,野猪又来作难,填饱肚子都不容易;跑到镇上打斤油、买点盐要走老半天。” xiushui.Net “嗯,是苦啊。”我不禁想起了童有财来,想起了他左脚鞋上的那两个烂洞。太阳西斜了,一点热度也没有,从树枝里挤进的秋风,渐渐地让我感觉到了凉意。回首望去,只见山头堆着山头,凝重冷峻,静默无语。父亲是对的,“生活难哪,没有谁是容易的。” “走啊!趁早啊!”父亲打断了我的思路,将身半蹲,左手撑在左膝上,右手捥在扁担上,将身一拧,挑起担子闪了闪,又小心翼翼地走在前头。 (八) 过了南山,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古老的樟树林静立着送我们离开,慢慢模糊成一团黑影。山道附近的村舍里,牛叫羊叫狗叫声清晰地传来,还有老妇人拖着长长的尾音,呼唤着顽皮的稚童回家。 父亲的脚步显得沉重起来,没有了之前的从容;我掉在他二十米开外,依然听得见他急促的喘息声,宛如风括过树梢。而我呢,几乎迈不开步子,担子莫名地变重了,刚搁到左肩,左肩立马一阵酸痛,强忍住挪了二三十米,便举双手托着扁担以减轻对颈窝的摩擦,咬着牙换到右肩,右肩又立马一阵酸痛。 “跟上啊,趁天还光多走几里,夜里更难走哦。”父亲间或停下来等我,瘦小的身躯上担着一个硕大的A字,湿漉漉的脑袋从A字中间凸出来,显得滑稽可笑。待我走近了,他再往前挪步;脚步虽不快,却还沉稳。我知道他的担子至少比我的重二十斤,我难以理解,那瘦小的身板竟然有比我多得多的能量! 修水网 夜色越发浓了,上弦月苍白地挂在天幕上,几点星在秋风里颤抖。蛇下源大屋后面的山路,灰灰淡淡地弯在三仙岭脚下,仿佛是谁随手丢弃的裹脚布。我与父亲缓慢地在这条浅灰的破带子上挪动,艰难异常。我看不见父亲的背影,只听见他的呼呼的喘息声和沙沙的脚步声,还有自己肚子里咕咕响的声音…… 到了三仙岭埂上,我实在挪不开步子了,我们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一会。“还是教书轻松吧。”父亲看了看瘫软在草地上的我,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黑瘦的脸在烟火里闪现一下,疲惫中也有几分平静。“人活着都不容易的,有口气就得像鸡一样去土地里刨食。当年,我从学堂出来,田地里的活路不熟,遭了些罪,也怨天怨地的,但还是苦苦地撑过来了。” 父亲在县城读过中学,文革时搞大串连去过北京。“远远的看见毛主席了,向我们招手勒。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啊,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我喊得嗓子疼了几天哦。”每当父亲剃头时,都要和理发师傅讲古,不是水浒就是三国,不是三国就是他去北京看见过“老毛”。俩人扯起来你来我往、眉飞色舞、唾沫迸溅,听得我们一些小孩子痴痴傻傻的,也是记忆里快乐的片段。 “来,从你的担子里抽几块出来,加给我。”父亲的话将我拉回现实,他摸索着将我的担子拆散了!我慌忙爬起来,有点窘迫地想重新绑好。我知道父亲其实很累了,比我矮一头的个子,显得瘦削的身板,担子又比我的重好多,怎么还能加重呢? 本文来自修水网 “你是没担惯,我是受得住的。”父亲摁着我坐下,从我的左右两边各抽出四块来,加绑到他的担子上,再将我的绑紧,试了试重量说:“没轻多少。我们走吧,离家不远了。” 这段路我是熟的,父亲便让我走在前头,手电筒在父亲手里,前后有规律地划拉着,将我身前身后数米的黑暗挤走、冲淡。我感觉担子轻了些,压在肩上那种麻辣酸痛的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可父亲明显慢了,每走十几二十米远就要停顿下来,沉闷地哼一声将担子换个肩膀。我们走走停停,最后这五里多路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走完。 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也老了,我也终究没有离开三尺讲台。可那一次进山的情景像一株狗尾巴草一样的长在我的记忆里,每当工作生活中不如意时,它就会伸展开朴实顽强的枝茎,告诉我一一“生活难哪,没有谁是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