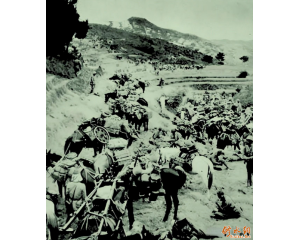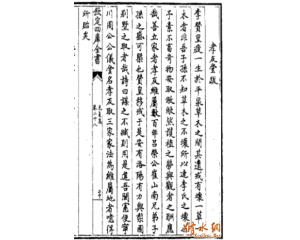|
据说,中国烟草公司是全世界纯收入最大的公司,却从不参与世界五百强排名。它那庞大的体量和超高的纯收入,可是咱中国广大烟民支撑起来的。所以啊,有的烟民不无骄傲地说:“中国的几艘航母和军队大批量的尖端武器,可都有我们烟民的贡献呢!” 不像茶和酒,唐诗宋词元曲里几乎找不到烟草的影子。仔细考证史料才知道,烟草是明朝万历年间从国外传入的。烟草起源于墨西哥,大概 3000 到 5000 年之前,墨西哥的玛雅人就开始吸食烟草了。1492 年,哥伦布的船队抵达古巴,发现当地人在吸食烟草,烟草随后就传入了欧洲。后来,烟草又分别从欧洲、日本、印度尼西亚传入中国。明代张介宾的《景岳全书》里记载:“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这就说明,烟草在明万历年间最早出现在福建、广东一带。  吸烟,在我们修水叫恰烟。 记得小时候在嫲嫲家住,我就睡在嫲嫲的脚头。嫲嫲烟瘾可大了,每晚睡觉前,都要坐在床边,就着昏黄的灯光,用水烟筒“咕噜咕噜”地恰上五六筒烟,那烟雾在她身边缭绕,仿佛是她一天劳累后的慰藉。早上起来,她先在床上坐好,披上衣服,又要恰上七八筒烟才起来刷牙洗脸,准备早饭。现在,周边的朋友一天恰两三包烟的也大有人在。 周湖岭 嫲嫲烟瘾大,公公也是个资深烟民。公公身子骨比较弱,在我的印象里,他几乎都在床上,下地的情况很少。他和嫲嫲各有一个水烟筒,你恰你的,我恰我的,互不相犯。那烟筒都是精铜铸制,底座沉稳,烟嘴细长稍弯,特别美观。他们两人都很讲卫生,烟筒一年四季都擦洗得黄光锃亮。他们自己不种烟,也收不了烟叶,但在六七十年代那么困难的时期,吸的烟丝却好像源源不断,从来没断过“粮”。为啥呢?因为我三个大伯三个姑父轮流着给他们送烟丝,而我父亲当时在全丰公社工作,也时不时买些烟丝回去。 有两个伯父住在老家,他们都种了一些烟草。烟草成熟后,就把整棵整棵的烟草收回来,挂到屋檐下晾干。用的时候,把叶子扯下,将叶子柔软的部分从叶子的筋脉上撕下撕碎,然后进行揉搓,再加点茶油或菜油继续揉搓,最后压到用坚硬木头特制的烟捆(有的地方叫“烟榨”)里,再用木工刨来刨,刨下来的就是一丝一缕的烟丝。 当时生产经营都是集体,自留地很少,都用来种菜和种猪饲料了,难得有闲土来种烟草,所以,烟丝就成了个难题。有些人没土种烟,又没钱买烟,可烟瘾又大,就只好用干豆子叶等适当的干叶子做烟丝,暂时解解烟瘾。 我们家在全丰公社的塘城街上住了十年,父亲在公社工作。公社每次开完会,我们几兄妹就会抢在扫地的人之前,到会议室的地上捡拾烟蒂。会议开得久,烟蒂就特别多,有时候甚至能捡到五六十个。那个时代的卷烟,没有现在的海绵过滤嘴,恰到半寸长的地方就只好扔掉,这扔掉的就是烟蒂。回家之后,我们把烟蒂里的烟丝剥出来,再从公社卫生院要来装针剂的纸盒,把烟丝一盒一盒地装好。外公一来,我们就把几盒烟丝捧出来,外公感动得几乎落泪。 本文来自修水网 父亲三十五岁之前也恰烟,烟龄超过二十年,后来戒掉了。他恰烟时,买的烟好像是《庐山》《欢腾》《飞马》这些二三角钱一包的烟,像几分钱、角把钱的《经济》《海鸟》《大公鸡》《黄金叶》这些烟,他好像没恰过。至于五六角钱一包的《大前门》《上海》,那得等到过年时才能买几包招待客人,而且还得弄来烟票才能买得到。 父亲曾经自制过卷烟,我还给他打过下手呢。他请做细木的木工,按自己的设计做了一个精巧的木制卷烟机,纯手工操作。从县城买来卷烟纸和烟丝,还有粘纸的糨糊。一个晚上做两个来小时,就能做出一百多根卷烟。那做好的烟堆在那里雪白雪白的,烟丝散发出的香味让人沉醉,除了两头稍微有点空之外,和供销社卖的烟没啥两样。 父亲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彻底把烟戒掉了,以后也没再恰过。戒烟的原因,一是恰烟对身体不好,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咳嗽一阵,咳出的痰黏黄浓稠,看着挺难受的。二是经济负担不起,一天最少要两包烟,就得四五角钱,一个月下来就是十多元钱,当时全家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五六十元钱,这十多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父亲恰的烟基本上都是卷烟,要么买要么自制。而其他人大多恰黄烟,也就是烟丝。在家就用水烟筒,出门就用烟斗。 湖岭 烟斗一般都是自己做的。在山上找一根大拇指粗细的小山竹,在离地尺把高的地方砍断,连蔸挖回。把竹蔸留一寸左右,其他的去掉,竹蔸上的竹棍留六七寸长,用细小的铁棍把竹节捅通,在竹蔸上挖个窝孔,让它和竹棍的中孔相通,再在竹蔸上的窝孔里衬上薄铁皮,烟斗就做成了。把烟丝按在窝孔上,点上火,含着竹棍这头吸。烟斗用的时间长了,因为指头手掌的摩挲、汗水的洇渗,会出现锃亮的油光,就像宝物的包浆一样。那时走集体,大家一起干活,工间歇火时,席地而坐,一个烟斗,一包烟丝,大家轮流恰烟,轮流“讲古”,那一时的疲累就在这氤氲的烟雾和阵阵欢笑中烟消云散了。 有的人因为条件限制,买不起水烟筒,又懒得做烟斗,图方便省事,就常常揣几张小孩用过的练习纸或几片旧报纸,歇火时,就用纸卷成烟卷,用唾液黏贴,那烟卷往往一头大一头小,大家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喇叭筒。 我虽然从没恰过烟,但也没少和烟打交道。 在桃树工作时,家住粮站。晚上时常有几个相熟的桃树街上的人跑到粮站会议室来打扑克,输赢的筹码就是烟卷。一次输赢出一到二根或三根烟,每个人面前都堆了白花花的一堆,起码都有三四十根。 在单位时,客人来了都要发烟,一开始是一根一根地发,后来风气变了,就一包一包地发。那时乡下没什么好烟,只有《芝城》《酉水》《银象》。后来到了县城,下乡或到单位上,大家发的烟就不一样了,都是《阿诗玛》《红塔山》什么的。我不愿要,主人就会劝说:“自己不恰烟,家里总会有客人啊!留着待客吧!”我就半推半就地收下,存下几包就拿到店里换点食盐酱油、肥皂牙膏什么的。 本文来自修水网 周边有很多同学朋友都恰烟,大家在一起时,我往往弄得一身烟味。妻子的鼻子特别灵,一进门就埋怨,说连毛线衣、内衣都是烟味。我却什么味道都没闻到,也许是鼻子失去嗅觉了,也许是“久居鲍鱼之肆不觉其臭” 吧! 现在,注重身体健康、讲究养生的人,对恰烟可在意了。自己不恰,要是周边有人恰,就会毫不掩饰地一脸厌恶。要是聚会休闲,都会问好谁恰烟谁不恰烟。恰烟的人也比较自觉,中途不恰,休息时就到合适的地方去过过烟瘾。现在公共场所,几乎看不到恰烟的人了,尤其是高铁站、高铁车厢里,这或许是处罚严厉,或许是大家的素质提高了的缘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烟的质量也大大提高了。稍低一点的有《金圣》《利群》《金芙蓉》《七匹狼》,较好的有《青花瓷》《黄鹤楼》《1914》《云烟》《中华》。总之,烟草品牌众多,全国有很多名牌产品,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当家品牌。烟草质量普遍提升,过去自种的烟丝没了,烟筒、烟斗也看不到了,大家恰的都是买的卷烟。烟的价格也像登山一样步步高升,有一两块的,有六七块八九块的,十几二十几三十几的都有,最贵的顶级烟能卖到百把块。物价部门未限价之前,有的一条烟据说能卖到几千上万元。 恰烟是传承了几百年的生活习俗,也是一种传统的“饮食” 文化。国家提倡不恰烟,但除了公共场所,也没有全面禁烟,所以,恰不恰烟还是个人的自由。 湖岭 恰烟对身体有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恰烟也有一些好处。它可以促进社交,递上一根烟,一下子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它还可以提神,在进行脑力劳动头昏脑涨时,一根烟能让你思路清晰;它也能解乏,劳动之余,一根烟可能会让你满血复活。所以,很多名人伟人都恰烟,像毛泽东、邓小平、鲁迅等等。 恰烟,不提倡不禁止;恰或不恰,悉听尊便。 2025 年9 月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