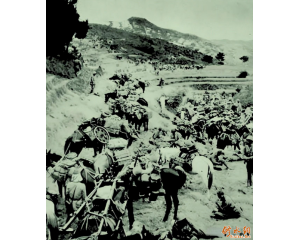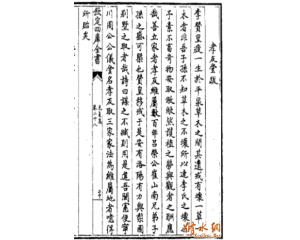(义宁陈氏故居——修水县宁州镇桃里竹塅陈家大屋)
修水的山,是藏着故事的。修江水蜿蜒西来,将湘赣边界的云雾揉进溪谷,也将一段跨越三百年的文脉,轻轻搁在了义宁州的土地上。当清雍正八年的风掠过闽西客家迁徙的烟尘,陈公元带着义门陈氏的血脉踏入这片山坳时,或许未曾想到,他扎下的不仅是家族的根脉,更在百年后与阳明心学的星火相遇,点燃了一个家族经世济民的精神明灯。 一、义宁陈氏的初垦与文脉初萌 闽西的客家山歌尚未在耳际散尽,陈公元已在义宁州的山林间结下了栖身的棚庐。这位义门陈氏 113 世后裔,带着客家人特有的坚韧与耕读传家的执念,在这片 “八山半水一分田” 的土地上开启了崭新的人生历程。娶妻生子,四子承欢,克绳、克调、克藻、克修的名字,像四颗饱满的种子,落在了亟待开垦的文化土壤里。 长子克绳的人生,藏着传统士子的典型轨迹。早年埋首书案,却屡试不第,便转身隐于山林。但他未曾让家族的文脉断绝,反而在主持分家的《分关》文书里,为子弟科考定下了细致章程:赴州府乡试者补盘费,取功名者重奖。那一笔笔关于读书的约定,不是对科举的执念,而是对“修身齐家”理念的朴素坚守。他知道,在这山高路远的地方,唯有知识能劈开蒙昧,唯有文脉能撑起家族的脊梁。 本文来自修水网 克绳的第四子伟琳,即陈琢如,真正让义宁陈氏的文脉有了精神内核。这位日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父亲,骨子里流淌着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热血。当他看到义宁州客家子弟求学无门,便牵头创办梯云书院,率先捐出 320 两白银,后又以父亲陈克绳名义添捐 100 两,在义学捐助中以长子树年之名捐 300 两,再给书院宾兴会补捐 25 两。四年间 745 两白银的投入,在清代中晚期足以购置百亩良田,而他却毫不吝惜地投向教育,因为他懂得,书院是“致良知”的道场,是让山民子弟“知善知恶”的启蒙地,是客家丕振起衰的新起点。 梯云书院的匾额在山风中轻颤时,陈伟琳的足迹已遍布大江南北。他“涉江揽金陵之胜,东历淮徐,北至京师”,所到之处不恋风景,只“考山河扼塞,校户口多寡,推古今因革之宜”。这种经世致用的游学,恰是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生动实践。而他对阳明书的偏爱,更成了家族精神的定盘星:“近世俗子支离,如浮沉大海中,不识所向,则阳明诚救时之学也。” 在郭嵩焘为他撰写的墓志铭里,这句肺腑之言,道尽了一个客家士子对心学的深刻体认, 心学不是空谈义理的玄学,而是指引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陈伟琳的一生,用三件大事诠释着阳明学说“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真谛。创办团练,是为保境卫民,在乱世中为乡邻撑起平安伞;创办书院,是为教书育人,让良知之光照进山野;穷究医学,是为治病救人,以仁心缓解生民疾苦。陈寅恪晚年回忆“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那句“中医之学乃吾家学”的感叹,藏着的正是陈氏家族“医人医世” 的初心。医人是救个体之疾,医世是救社会之弊,而两者的源头,都是阳明心学“致良知”的召唤。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二、陈宝箴“知行合一”的实践 陈伟琳的精神火种,在三子陈宝箴身上燃成了燎原之势。这位被曾国藩誉为“海内奇士” 的晚清重臣,自少年时便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浸润阳明心学,将“心即理” 的哲思化为“知行合一”的为政之道。 光绪元年,陈宝箴赴任湖南辰永沅靖道台,治所设在凤凰厅。彼时的湘西,山高林密,民生凋敝,土司旧习未改,百姓告状无门。陈宝箴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畅通小民告状渠道。他脱去官服,常到乡野间倾听民声,断案时不徇私情,只凭良知与公理。很快,凤凰厅便流传起“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找陈道台”的俗语。这句朴素的赞誉,比任何官样文章都更能证明他“为善去恶”的实践。 湘西多山,红薯是山民的主粮,却因鲜薯不易保存,常遇丰年烂在窖中的困境。陈宝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根据家乡义宁州老百姓的一贯做法,将红薯刨丝晒干的保存方法传授给山民,并手把手教山民操作。那晒得金黄的薯丝,不仅解决了粮食存储难题,更让山民懂得:致良知不必惊天动地,于细微处解民之困,便是格物致知。 沱江穿凤凰而过,很多河段乱石阻滞,有的地方常年淤塞,山货外运不畅。陈宝箴决意疏浚河道,可府库空虚,经费无着。他没有向上级伸手,而是回家劝说老母亲,将私房钱悉数拿出充作工费。河道疏通那天,沱江的水波载着木船顺流而下,山民的笑声与船工号子交织在一起,而陈宝箴调离凤凰时,却清贫到无钱雇船赴新任。这种“苟利民生,不避困穷”的担当,正是阳明“知行合一”最动人的注脚。 
(欧阳国泰老师在为学生讲述义宁陈氏故事)
光绪年间,陈宝箴再赴湖南任巡抚,此时的他,已将阳明心学的经世精神推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彼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在湖北推行洋务,陈宝箴与之呼应,在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新政。他深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是空谈,而是“致良知” 在变局中的新实践。良知不仅要明善恶,更要知时变,唯有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方能救国图存。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在湖南,陈宝箴雷厉风行。“董吏治以正官风,辟利源以兴实业”,开办邮局、电报打通信息脉络,建发电厂、自来水厂引入现代文明,更设时务学堂培育新才。他深知“变士气,开民智”是新政的根基,便广纳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让湖南一跃成为全国维新变法的重镇,更为意义深远重大的是启蒙了湖南人的家国情怀和培育了开风气之先的精神。这些举措,看似是对西方技术的效仿,实则是阳明“心即理”的延伸。心之所向在强国富民,便不拘一格取法中外,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大智慧。 三、陈三立与陈寅恪的精神坚守 维新变法的烈火最终被守旧势力扑灭,陈宝箴被赐死,陈三立的政治生涯也戛然而止。这位曾协助父亲推行新政的热血青年,带着无尽的悲愤退隐山林,却将家族的精神火种播撒在了诗歌与气节的土壤里。 陈三立的诗,被誉为“同光体”的巅峰。他的笔触里没有风花雪月的闲愁,却有山河破碎的痛感与文明存续的执着。“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看似闲淡的诗句,藏着的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经世情怀。这种将家国大义融入诗词的创作,恰是阳明“致良知”在文学领域的体现。良知不必借朝堂施展,在笔墨间坚守正义,在文字中传承文脉,亦是“为善去恶”的践行。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1937 年,日寇占领北京,年逾八旬的名士陈三立成了侵略者拉拢的对象。汉奸与日寇轮番上门,威逼利诱他出任伪职,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始终严词拒绝。“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绝不做亡国奴!”他关闭门户,拒食拒饮,用生命诠释着何为“知善知恶”。七天后,老人溘然长逝,那股宁死不屈的气节,正是阳明心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精神写照。当良知与民族大义相连,生命便可化为照亮后世的火炬。 国民政府为褒扬其忠烈,将当时驻扎在修水漫江乡的省立赣西北临时中学更名为“江西省立散原中学”。如今,“散原中学”的校牌仍在修水县城紫花墩上熠熠生辉,那不仅是对一位诗人的纪念,更是对义宁陈氏“以气节立世”精神的传承。 陈氏文脉的香火,在陈寅恪身上化作了更深沉的学术坚守。这位被誉为“史学大家” 的学者,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八个字的内核,与阳明心学“心即理”的哲学一脉相承。阳明说“心外无物”,陈寅恪则用一生证明:学术的真理不在权势的威压里,不在世俗的喧嚣中,而在内心对知识与良知的坚守。 在双目失明、饱受病痛折磨的晚年,陈寅恪仍坚持口述著述,完成《柳如是别传》等皇皇巨著。他在书中为明末清初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实则是借古人之迹,阐发“独立之精神”的可贵。这种在绝境中坚守学术操守的执着,恰是阳明“知行合一”在学术领域的极致体现。知学术之贵在求真,便穷 湖岭 陈寅恪曾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这份对真理的执着,与陈伟琳创办书院的初心、陈宝箴推行新政的担当、陈三立宁死不屈的气节,共同构成了义宁陈氏的精神谱系。而这条谱系的源头,正是阳明心学那盏“为善去恶”的长明心灯。 从陈伟琳在桃里竹塅宅院诵读阳明之书的晨钟,到陈宝箴疏浚湘西凤凰沱江的号子;从陈三立绝食明志的风骨,到陈寅恪病榻著述的灯火,义宁陈氏的百年传承,恰似一条奔流不息的河,而阳明心学便是河床下的磐石,支撑着河水始终朝着“致良知”的方向流淌。 修水的山依旧青翠,梯云书院的旧址虽已湮没在岁月里,但那“知行合一”的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当我们重温义宁陈氏的故事,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生命力——阳明心学不是故纸堆里的教条,而是能穿越时空的智慧,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只要守住内心的良知,践行“为善去恶”的准则,个体的生命便能与时代的脉搏共振,家族的文脉便能与民族的精神同辉。 心灯不灭,文脉便不会断绝。义宁陈氏与阳明心学的相遇,早已超越了家族史的范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 那盏在修水桃里竹塅山坳中点燃的良知之灯,终将在岁月的长河中,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 本文来自修水网 2025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