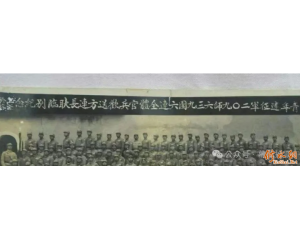|
一天午后,我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刷到抖音里一段踩打谷机的旧影像忽然撞入眼帘。隆隆的机声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那是儿时“双抢”的声音啊。“双抢”这两个字,大抵只有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生人才能咂摸出其中的滋味。 时令刚过六月,早稻已染得田野一片金黄。大暑前后的天空,净得像被雨水洗过的蓝玻璃,透亮得晃眼。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突然变得格外精神,“八一拿下双抢关”的口号一遍遍炸响,像出征的号角,催得人心头发紧。一年一度的“双抢”,就这么拉开了序幕。  “交秋脱伏,晒得肉熟”,说的就是这时候。“双抢”是一年里最热、最忙、最累的日子。开战前,每个生产队都像要上战场的军队,把镰刀磨得锃亮,抽水机调试得顺顺当当,晒谷场扫得连草屑都不剩。随后开动员大会,干部、老师、学生,连赤脚医生、供销社的营业员都放下手头活计,男女老少齐上阵。分工明明白白,责任落到人头,按劳动量记工分。我们那儿有句俗语:“烟哉栅上的人都要操下来”,意思是连最清闲的人都得动起来,可见这仗打得有多紧。 本文来自修水网 二十天,就二十天时间,要把熟了的早稻全割完,田犁好,再把晚稻秧一株株插下去。晒谷、施肥、打药、抽水,哪样都得跟上,半点含糊不得。 六十年代末才出现的打谷机,在那会儿可是宝贝。踩打谷机是真累啊,两个人像拉车的牛马,脚死命往下蹬,手里还得攥着禾束往滚筒上送。四个人轮着来,稍一松劲,滚筒就慢下来,甚至停了,哪敢歇?打谷机旁总围着八九个男劳力:四个打禾,一个捆稻草,一个清谷粒,一个挑谷去晒场。割禾的多是妇女和学生,看着不用费脚力,可一整天弯着腰,像地里的蜜蜂似的穿梭,直一下腰都怕被别人甩在后面——定额计酬呢,谁愿落人后?我还记得小时候跟伙伴们比着割禾,一不小心,左手小指被镰刀划开个大口子,至今指甲盖还是两瓣的。 “走杂”算是双抢里的“轻省活”,从各组抽调的劳力拿全队平均工分,耕田、晒谷、施肥、抽水的都算,还有打石灰的、拖架子的、记工分的。公社干部和农技员常来田埂上转,像指挥官似的查进度、教技术。 割禾的日子忙得脚不沾地。上午收工,得先把田里的禾秆一把把拖上岸。最怵的是中午,日头像个大火球烤着,还得挑上百斤稻谷去公社粮站交公粮。扁担压得“咯吱”响,每一步都费劲。路在烈日下晃得人眼晕,汗湿透了衣衫,后背结出层白花花的盐,谁也顾不上擦,就想着赶紧把公粮交了。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小孩子也闲不住,割禾、扯秧、拖禾秆,再皮的孩子到了这时候也得乖乖干活。晒谷更是麻烦,那会儿没水泥场,全靠“地箕”(晒垫)。翻谷、扫禾衣,中午要换地方晒,挑进挑出,没一刻消停。最怕的是午后闷雷,保管一喊“要下雨啰,收谷啊”,所有人都跟听见紧急集合哨似的,抓起扫把、箩筐就往晒谷场冲,手忙脚乱地把谷堆起来,生怕一场雨把辛苦收的粮食泡了汤。 早稻割完,紧接着栽晚禾。主力还是妇女和学生,那会儿没插秧机,全靠手一株株插。弯一天腰,技术好的能栽八九分田(十分为一亩)。栽禾记的工分是平时的三倍,可也不好混——得按“四六寸”的间距插,有人拖着“架子”在田里划格子,跟在方格本上写字似的,半点偷工减料都不行。 二晚插秧时,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下午的太阳像个白花花的火球,热浪裹得人喘不过气。脚下的水田像口大蒸笼,热气直往上冒,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滚,脖子上搭的汗巾早就湿透了,身上没有一根干纱。中暑、拉肚子是常事,我就拉过几天痢,吃什么拉什么,最后拉的都是白乎乎的黏液,可还是得下地,哪能歇? 黄昏天凉点了,蚊子、麻蝇又成团地扑过来,闻着汗味就叮。田里的蚂蟥更气人,悄没声地吸在腿上,一扯就是道血口子。晚上也不得安生,放水、抽水、扯夜秧,打药、抗旱、整田,照样忙到深更半夜。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不过苦里也有乐子。有人捆完稻草,站在滚耙上唱《娇莲》山歌,调子悠悠的,听着倒也能解点乏。 如今农村大变样了,那紧张繁忙的“双抢”,像部老电影,慢慢淡出了视线。可对我来说,那段日子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是一辈子用不完的精神劲。每次想起来,心里总像打翻了五味瓶,有怀念,有感慨,还有股子说不出的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