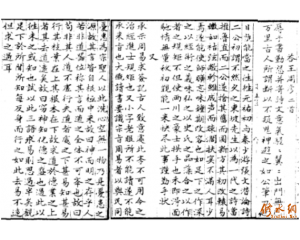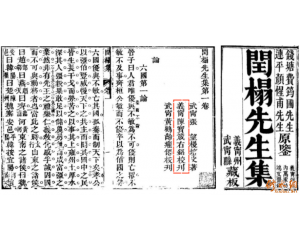|
一、“阳鸟夷”“三苗”(尧舜禹时代至夏朝) 大约在4500年以前,赣北的的人类活动基本上处于蛮荒和蒙昧状态。之后就出现了“阳鸟夷”“三苗”。从4500年以前到4000年前(也即从黄帝到夏朝建立)的500多年内,“阳鸟夷”、“三苗”成为赣北民族的主体。 “阳鸟夷”以太阳鸟(即天鹅之类)为图腾,而根据学者阐述,“三苗”的“苗”是一个象形字,相当于一个插着羽毛的帽子,体现了对鸟的崇拜,与“阳鸟夷”有类似之处。《尚书·禹贡》及《史记·夏本纪》云:“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鸟夷卉服。”“阳鸟夷”、“三苗”演变为后来的苗族,往西南一带迁徙,但长江以南仍留有后裔。《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今佛书中有此人,即鸟夷也。”郭璞生活在两晋时期,主要活动江州、扬州一带。 实际上,阳鸟夷更早居住在鄱阳湖流域,而三苗是后来才来到南方的,他们来到南方,征服了阳鸟夷,就合成了一族。 炎黄大战之后,炎帝部落的一支聚居于鄂西北、豫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毗邻,建立了三苗国。三苗国是中原王朝的强劲对手,从颛顼、帝喾,一直到尧、舜、禹时代,屡次与中原王朝展开大战,但每次大战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不断南逃,到达南方的“南海”、“三危山”,与先期到达南方的各个部落汇合。 周湖岭 《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东,汇泽为彭蠡。”这个“南海”显然与“彭蠡”相距较近,不是现代的“南海”。而 “有苗之民叛入南海”,更不可能是叛逃到了广东或海南岛一带。《尚书·禹贡》所说的“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其中的“黑水”、“三危山”,都应当在云梦泽附近。“三危山”可能就是大别山。《诗经·大雅·江汉》提到了“南海”:“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参考传世的周代青铜器召伯虎簋铭文以及《后汉书·东夷传》,此诗应指周宣王之时召伯虎率军征讨江汉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诗中的“南海”,无疑靠近“江汉之浒”,亦即长江、汉水之滨;而同为“江汉之浒”的地方,就在现代的武汉地区。这首诗或可表明,当时的“南海”离武汉不远。又《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国率领诸侯伐楚,楚王派人对齐侯说:“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总结起来,三苗之民往南逃到云梦泽附近,在这里建立了国家,征服了“阳鸟夷”,“阳鸟夷”也就成为“三苗”的一支了。 本文来自修水网 在此之前,南方的民族被称为“阳鸟夷”,尚无“三苗”之称。而三苗国南迁之后,南方民族都被称为“三苗”了。之所以被称为“三苗”,可能是指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部落氏族。有人说,“三苗”指“有苗”、“苗民”及“苗蛮”,这也反映“三苗”是由不同部落组成的。 大禹征伐与自然灾变 舜帝即位之后,命令大禹讨伐三苗。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对大禹说:“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指舜帝命令大禹率兵征伐三苗。之后大禹“乃会群后”,即带领各个部落首领,誓师出征。此次出征,得到伯益的大力支持。从“七旬,有苗格”一语可知,这次战争历时七十天,以大禹大获全胜而告终。 大禹出兵之时,三苗国恰逢大灾,乱象丛生,民心不稳。《墨子·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有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根据上述记载,三苗亡国之时,时值夏天,出现了“雨血三朝,龙生于庙”、“夏有冰,地坼及泉”以及“昼日不出”等自然现象,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与混乱。其中“雨血三朝,龙生于庙”可能是指刮起了龙卷风,同时带来了“红雨”。在天灾频发、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三苗国几乎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面对大禹的军队一触即溃。《墨子·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这可能指交战之时,雷电大震,大禹手下有一位打扮成人面鸟身神灵模样的将领,一箭射死了有苗的头领,有苗军队大乱,被大禹一举击败,三苗国也就覆亡了。 周湖岭 三苗国灭亡之后,残存的民众逃入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山区之中,应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山地小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也就是说,西至岳阳、北至武昌、东至九江这一片广大的赣北山区,乃是“三苗”聚居的主要地域。 南宋之时,朱熹《记三苗》引詹元善语云:“苗民之国,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兴国军,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难出。最后在今之武昌县,则据江山之险,可以四出为寇,人不得而近之矣。” 《墨子·非攻下》:“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明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大意是说,大禹战胜三苗之后,就划分山川,区分事物,节制四方,造成了神民和顺、天下安定的局面。据此可知,大禹征服有苗之后,就着手对南方进行治理,反映这一历史的基本材料就是《尚书•禹贡》。 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得王位,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王位之先河。夏朝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夏朝期间,逃入赣北山地的三苗应该建立了一个山地小国。他们应该也给夏朝进贡,但总体来说与外界隔绝,不相来往。 山背遗址位于江西修水县上奉乡山背村,包括跑马岭、杨家坪等43处遗址,主要分布于跑马岭、养鸭场、金鸡岭、长窝岭、风洞嘴、杨家坪、刺毛窝、荷树窝等8处山坡上,面积约6200平方米。上层为商代遗址,下层为新石器晚期遗址(新石器晚期距今约5000—4000年),文物堆积保存较好,包含物丰富。1960年以后进行了初期发掘,获得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出土的石器有锛、斧、镞、铲、凿、网坠、镰、球、蛋、励石等。出土的陶器有鼎、鬹、豆、壶、罐、簋等。有人推断,山背文化应该是三苗部落的文化遗存。考古资料表明,他们以种植水稻为主,以采集和渔猎为辅,同时纺纱织布,制作衣服,采用木骨泥的结构建造住房,用木棍、泥土和稻草杆做成“三合一”的墙壁,顶上盖草或树皮。这个时期制陶技术亦佳,陶器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好,基本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百濮与九菌 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后”即君主),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商朝约存在于公元1600年——公元前1100年,前后相传17世31王,为西周所灭。 本文来自修水网 有关商人南侵的史实,古史屡有记载。《孟子•滕文公下》云:“(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古本《竹书纪年》曰:“汤有七名而九征。”今本《竹书纪年》曰:“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吕氏春秋•异用》:“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以上史料说明,早在成汤时,商族势力已长驱南下,征服了南土长江中游的大、小部族,使之皆臣服于商,为此长江中游已属于商朝的南土范围。 夏商两代在赣北地区留下了许多痕迹,而商代留下的烙印尤其深刻。如武汉盘龙城,瑞昌商周铜矿,樟树吴城遗址,九江的荞麦岭遗址等等。德安境内有大量商代村落遗址。最大方国(相当于后来的诸侯国)在樟树吴城,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就是著名的“虎方国”。 修河流域已经被商代方国统治,山区的三苗后代,有了另外的名称,叫做“百濮”“九菌”。《逸周书·王会解》:“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九菌国在赣北境内,是殷商时期的方国之一。百濮,是濮人的通称。《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大饥。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清代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百濮属于南方蛮夷的一种,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没有统一的政权:“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晋朝建宁郡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晋建宁故城在今湖广荆州府石首县,当时麇人所率百濮在其南。”巴蜀一带也有百濮:“巴中七姓有濮。此又别一濮,盖百濮之散处者耳。”综合起来,百濮之名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延续至春秋犹存,他们的居住地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有些变迁,大地居住在长江中游以南的山区,上至巴蜀,中至湘西、湘东,下至鄂南、赣北。春秋时期,百濮屡屡与楚国对抗,亦可见他们的居住地大抵在楚国周边,但主要是在楚国的南部。从商王朝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九菌”还是“百濮”,都属于山地部落,除了进贡一些方物之外,没有更大的意义。真正体现商王朝对南方经营成果的,还是由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南方方国。 本文来自修水网 商朝时期赣北的九菌国,应该位于靖安县一带(下面还要讨论这一问题)。“菌”既是国名,又是他们的贡品,实际上应该是“箘”(一种做箭杆的竹子)。与此同时,修水的三苗部落应当还存在,但力量已经很弱小。从后代的记载来看,九菌国与艾国有很明显的亲缘关系,应该都是三苗国的后裔。 麇子国的出现 “麇,有“qún”“jūn”两种读音。按《康熙字典》,“麇子国”读作“君子国”。实际应该与“九菌”的“菌”同音。 武王伐纣之后,商朝灭亡,但南方的虎方国依然忠于商王朝,不服从西周的统治。西周之后,周康王(第三任)、周昭王(第四任)发动了大规模的南征,消灭了虎方国。虎方国被打败之后,遭受了类似于屠城的灭顶之灾。吴城遗址中留下的残骸,可能就是这两次战争中不及逃走而被杀的虎方国臣民。虎方国的文化因此而戛然终止,吴城遗址没有出现周初以后的遗物,表明这一都邑在西周之初已被彻底毁灭。 虎方国被灭之后,西周王朝把赣北的百姓迁徙到庐山脚下,同时继续掌控瑞昌商周铜矿,依靠武力逼迫百姓从事繁重的矿山开采业。九江县新合乡发掘的神墩遗址,以西周文化堆积层为主,表明这里是西周百姓聚居的地方,这一地方位于瑞昌商周铜矿遗址和荞麦岭商周遗址之间,聚居在这里的人们应当以开采矿山和冶炼青铜为主业。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综合德安县的文物考古成果,这一带商朝时期的文物十分丰富,已经发现的商朝文化遗址有三十多处,而西周早期的文物,却十分罕见。由此可以推测,德安县一带是商朝臣民的聚居地,但是到了西周初期,这些居民也被迫迁走了。 虎方国被灭之同时,位于靖安的九菌国也被灭了,山民也被掳掠去开矿了。位于修水山背遗址的三苗部族也被灭了,山民也被掳掠去开矿了。从“麇子”“艾子”这两个称号来判断,西周灭了九菌、三苗,但没有完全摧毁这两个部族,而是把九菌迁徙到靖安县的偏僻山区(原来可能在修河边上),把三苗迁徙到更偏远的修水渣津一带,将国王分别封为“麇子”和“艾子”。因为“公侯伯子男”的封号,只有周天子才有权赐予。楚国国王长期只有“楚子”的等级,他是没有权力封“麇子”和“艾子”的。 1981年,大田大队修水库时出土了一枚西周甬钟。拥有西周甬钟者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有较高等级的人物。可以表明西周已经征服了修河两岸地区,位于修水山背遗址的三苗后裔被迫迁徙到更远的山区。 周昭王(公元前995—977在位)曾经讨伐过虎方、桧、楚国,可谓战功赫赫,但二十四年伐楚之战,却遭遇惨败。不但他所率领的六师被消灭,昭王自己也溺毙于汉水。继任的周穆王讨伐南方,又遭惨败。从此之后,西周越来越弱,失去了对赣北的控制权;楚国越来越强,不断往东扩张。而位于赣北的麇子国、艾子国,也就与楚国不断发生冲突,最终被迫臣服于楚国了。这时候,散布在麇子国、艾子国周边的部落民族,被称为“百濮”,他们一同加入了反抗楚国的斗争。 周湖岭 第一阶段:麇子国与楚国翻脸 《左传·文公十年》记载,楚穆王九年(前617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打算攻打宋国,而“麇子逃归”,亦即跟随楚国的麇国君主逃回了自己的领地,打乱了楚国的计划。楚国非常恼火,到了第二年春天,“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潘崇复伐麇,至于锡穴。”这一事件表明麇子国的独立性还比较强,有一定的实力,楚国这才会胁迫他们去攻打宋国。所谓的“锡穴”,很可能就在德安县一带。楚国沿着水路来讨伐,从彭蠡泽进入修河流域是合理的。 在江西,锡矿的分布集中于赣南与赣北,如距离瑞昌商周铜矿不远的德安县,现代已探明的锡储量有9万吨,主要分布在吴山、丰林、林泉等乡镇一带。其中曾家垄(现彭山锡矿)的储量为2万吨,尖峰坡的储量为2.7万吨;红花尖的储量约2.4万吨,坡西、舒家、黄金洼的锡储量约有1.9万吨。 第二阶段:麇子国联合百濮等攻打楚国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在“楚子伐麇”之后六年,即楚庄王三年(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的部落诸侯借机发动对楚国的攻击,一时间戎人、蛮人、庸人、麇人、濮人从多方面形成了对楚国的攻击之势。楚国在秦人、巴人的协助下,集中力量灭了庸国,迫使群蛮、百濮惊慌四散,不得不重新屈服于楚国。 周湖岭 麇人率百濮攻楚,表明麇国与百濮所居地区邻近,故而可以结为同盟。有人认为麇子国在武当山附近,这是不合理的。一百多年之后,即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国大举进攻楚国,第二年退却之时,犹有“吴师居麇”的记载。这个“麇”显然就是麇国。吴国退回长江下游地区,怎么会往西北跑到武当山地区? 第三阶段:麇子国、百濮协助吴国攻打楚国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春秋左传正义》说:“吴在东,濮在南。”“百濮”处于南方,与楚国隔江相望,为此很容易为吴国所用,楚国也不得不认真对付他们。《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载楚平王四年(前525年),吴伐楚,楚国以水军大败吴师。楚平王六年(前523年)夏,楚平王组建舟师以伐濮,就是因为百濮协助吴国攻打楚国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在这次战役中,吴人的进军路线很值得关注,但史学家对此未能形成统一的见解。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率水师从淮河而上,到大别山西麓,再改从旱路下到武汉西面,渡过汉水去攻击楚国的首都。到了第二年(前505年),秦人出兵援助楚国。吴人屡遭败仗,不断退却。在这一战之中,“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婿之溪,吴师大败,吴子乃归。” 本文来自修水网 吴人败退时,沿着长江北岸返回武汉西南,这时就不必再回淮河,而是直接往武汉东南方向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其中“吴师居麇”的“麇”,大致也应该在武汉西南一带,即今天的咸宁地区。所谓的“吴师居麇”,或者意味着“麇”在这时已经成为吴国在楚地的大本营,粮草乃至兵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补给,故而吴人在连吃败仗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从容退却。 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国进攻楚国之战,使麇人、濮人得以扬眉吐气,然而吴国功败垂成,使麇人、濮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必然遭到楚国的疯狂报复。 第四阶段:麇子国的灭亡 从夏朝开始的“九菌国”、“菌人”,到春秋时期演变为“麇子国”“麇人”,遁入大山腹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故而有能力率领百濮伐楚。清朝朱鹤龄《读左日钞》说:“王使由于城麇。按传文,麇即是脾泄之地,因子西兽立国于脾泄,故筑城以旌之。《一统志》:故麇子国在岳州府境,有东、西二城,楚昭王使王孙城麇,即此。”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岳州,古苍梧之野(苍梧野不止于此,郡界侧近之地皆是),亦三苗国之地(亦古麇子国;春秋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即此地也。凡今长沙、衡阳诸郡,皆古三苗之地)。”根据这些说法,“麇子国”位于岳阳市,而岳阳市的山区临湘县一带,正处于幕阜山的北侧,与赣北的修水县接壤。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逸周书·王会解》:“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个“九菌”,当泛指南方以“菌”为号的部落。《山海经·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又《淮南子·地形训》:“突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 《山海经·大荒经》:“有小人国,名曰靖人。”郝懿行注引《说文解字》云:“靖,细貌。”“盖细小之义,故小人名靖人也。”又指出《淮南子》的“竫人”,《列子·汤问篇》的作“诤人”,也应该就是“靖人”。山地部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谓的“菌”、“麇”、“靖”、“诤”、“竫”应该都是发音比较接近的记音之词,是对同一部落或同一蛮夷的称呼,各种释义也未必准确。 江西北部的靖安县,地处九岭山之中,与靠近修河的武宁县仅一山之隔,据明郭子章《郡县释名》记载,“靖安”在唐代及其以前本是里名,唐代因里名乡,因乡名镇,五代十国时期因镇名场,因场名县,才成县名。可知“靖安”一名来历很早,是否与“靖人”有关?很有可能。 本文来自修水网 2007年初,在靖安县水口乡李洲坳,因盗墓贼而引发的古墓考古令人瞩目,次年这一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个墓葬共有47具棺木,有22具棺木发现有人类遗骸。出土各类文物650余件,其中竹木器144件,漆器12件,玉器13件,青铜器30件,原始青瓷器7件,金器1件,金属器5件,纺织品300余件。文物专家判定其年代当在春秋晚期,距今约2500年左右。2010年,靖安老虎墩遗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110多座新石器时代墓葬,还发现一条至少有5000多年历史的鹅卵石路,这也是江西省史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保存完好的第一条路,堪称“江西第一路”。如果考古成果足以征信,则可以推测靖安县的早期人类活动覆盖了夏商周三朝的历史,甚至更早。但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些墓葬的主人,所以人们作出了各种猜测。联系春秋晚期吴楚争战的历史,不妨认为靖安古墓与麇人有关。 文物考古判定的靖安县古墓的年代,与“吴师居麇”之事高度吻合,即距今2500年左右。靖安古墓的主人,应当就是麇子国的国主。如果靖安古墓的主人是楚国贵族,则他的葬俗、所陪葬的物品,应当与楚国贵族基本一致。但从文物考古的情况来看,其墓葬规模足以和楚国贵族抗衡,其葬品、葬俗却与同时期的楚国贵族迥异。这种身份与陪葬品不一致的情况,可以表明靖安古墓的主人属于另一个侯国的体系。同时期楚国的墓葬,用人殉葬的情况已经较少,即便有殉葬,人数也很少。在目前已发现的楚国墓葬中,大多数只有一到三人殉葬,仅有极少数例外。总之,楚国贵族不可能像靖安古墓那样,用多达22名的年轻女性来殉葬。总结起来,靖安古墓的主人,身份比楚国贵族更高,但所属地带的文明程度却不如楚国;这与“麇人”的历史记载是吻合的。靖安古墓的出现,也有可能是麇子国亡国之君的作为。在靖安古墓的主棺中,除了一只青白玉器外,并未发现其他物件。这有可能是在吴国败退之后,麇子国君被杀,抛尸于楚,麇子国亦面临灭顶之灾,故而国中臣民杀人为殉,为其国君建造一座纪念性坟冢,展现了这个山地部落的悲壮结局。从此之后,麇子国便彻底没有了影踪(有些人认为靖安古墓是徐偃王后代的墓葬,但在苏北发现的徐国君王墓葬,与中原风格非常接近,文明程度很高)。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艾国的延续 《雍正江西通志》卷三十八记载分宁县(今修水县)有古艾城,引《宋郡县志》云:“以县分自武宁,故名分宁,古艾地也。今县西一百里龙坪冈有艾城存焉。”引《左传》云:“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引《后汉书》云:“刘陵,艾人。”所指皆为古艾国之地。《乾隆宁州志》卷三云:“古艾城,在州西一百里崇乡四十九都龙冈坪,春秋时为艾子国,自汉以后,为艾县。隋开皇九年,省入建昌,今城故址犹存。” 如前所述,艾子应当是西周早期的封号。公元前515年,时值春秋后期,吴国发生王位之争,吴公子光派人刺杀吴王僚,抢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吴王僚的儿子公子庆忌出逃,居于艾,后入楚求助,准备发兵攻打吴王阖闾,却被吴王阖闾派来的刺客要离杀死。 那么,这个“艾”源于何时?宋代罗泌《路史》云:“艾,侯爵,穆鼎有‘艾侯作’,王俅以为共误,并之广阳,汉之上艾,后汉石艾也。又吴有艾县,隋入建昌,有艾城,今在武宁。”《路史》又曰:“武王俘艾侯、佚侯,小臣四百六是也,皆商国。”按《逸周书》:“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罗泌指出,艾国在商朝时为侯国,穆鼎(当指周穆王时的鼎器)铭刻有“艾侯作”的字样,但王俅以为“艾侯”当作“共侯”。山西并州的广阳县,就是两汉时期的上艾、石艾。如此说来,商朝的艾国,应当在山西境内。又根据《路史》和《逸周书》,周武王灭商,艾侯、佚侯等“小臣”皆被俘虏。 周湖岭 然而,周武王所俘虏的霍侯、艾侯,都应该在山西境内,与南方的“艾”似乎无关。西周初期,亦不见在南方分封艾国的记载。南方的“艾”,当属于久居南方的山地民族。 《国语·周语上》:“树于有礼,艾人必丰。”韦昭注:“艾,音刈。树,种也。艾,报也。丰,厚也。”“艾”读作刈,意思是报答。然而这一解释并不妥帖,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艾人”似乎有“恶人”之意,这两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为“如果以礼为立身之本,则‘恶人’也可以丰厚。”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午日悬蒲人艾人于门,以禳毒气。”“蒲人艾人”是指用菖蒲、艾草做成的小人,据说可以驱鬼去毒。明朝陈三谟《岁序总考全集》说端午之日“楚人采艾挂于门上,以禳毒气,今挂蒲艾是也”,也可说明“艾人”的用途。除了“艾人”,又有“艾虎”之说。明代刘若愚《酌中志》:“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毒故事,如年节之门神焉,悬一月方撤也。”“五毒艾虎补子蟒衣”,就是绣有“五毒”(指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和“艾虎”的衣服,将“艾虎”与“五毒”并列,可见它是一种凶恶之物。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宋代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九对“艾人”、“艾虎”的记载甚多。“端午刻菖艾为小人子或葫芦形,带之辟邪。”“荆楚人端午采艾结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端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明代《六十种曲·金雀记》:“朱砂写狰狞艾虎,试看毒魔惊讶。”元僧梵琦《楚石梵琦禅师语录》:“今朝五月五,艾人骑艾虎。”相传为诸葛亮、刘基所作的《奇门遁甲秘笈大全》:“凡敌兵暴至,必有赤云赫赫然,……或赤虹如狗,四枚相聚,如人行不绝,或如艾虎,或上有云,下有零螟,……皆主敌兵暴来袭我也。” 综合起来,“艾人”、“艾虎”皆为凶恶之物,所以被用于祛除恶物。“艾人”、“艾虎”都与“艾草”有关,但艾草是一种普通的植物,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却不足以和凶恶的“艾人”、“艾虎”联系起来。有一种动物叫“艾虎”,又称艾鼬,但它只是一种小型毛皮动物,不会给人以凶恶之感,且它主要分布在寒带,长江中下游并不常见。据此推测,“艾”应当是个地名,“艾人”属于山地民族,且对楚人造成过重大威胁,被楚人视为凶恶之物,所以后来被楚国人用作端午节的辟邪之物。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推测楚国人用来辟邪的“艾人”、“艾虎”,其中的“艾”当指位于修水县的古艾国。之所以选用艾草来制作,只不过因为“艾草”与“艾国”之“艾”同音同字罢了。同理,楚国人又用蒲草来制作辟邪的“蒲人”,也只是因为“蒲人”与“濮人”同音罢了。明朝杨慎《南诏野史》说:“蒲人,即古百濮,周书所谓微卢彭濮也,后讹为蒲。”“濮人”讹为“蒲人”,可见辟邪之“蒲人”的本意。德安县古称“蒲塘”,或当为“濮塘”之讹,指的是这里为百濮的居住地之一。 麇子国因反抗楚国而灭,但艾国却几乎不参与这些战争,因此相对平稳,得以保全。从文明程度来说,艾国比麇子国还要低一些,可能是“三苗”中最古老的一支。艾国的存在,是西汉初设立艾县的基础。 百越时期、秦朝 公元前473年,吴国为越国所灭。从现代发掘的文献来看,鄱阳湖以西的地区,基本上臣服于楚国;鄱阳湖以东的地区,基本上属于越国。公元前334年,楚威王杀越王无疆,越国灭亡,但它属下的小诸侯依然存在;又在此之后,史料中仍然时常出现越国,足以证明越国未亡。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地区称为“百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国灭亡,秦朝建立。 本文来自修水网 《史记·越世家》记载:“楚既灭越,越诸族子,散处江南、海上,或为王,或为君,服朝于楚。”南宋罗泌《路史·夏后氏纪》说:“越王无疆为楚所破,族散江南、海上,于越、东野……叠为伯长。”《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百越时期的200多年,修河流域相对比较平静。这时期楚国因攻占了重庆、四川、汉中等地区,对秦国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秦楚大战就不可避免。秦国一度攻入郢都。楚国衰落下去,对修河流域也就不太关注。这时期秦国出现了一个著名人物,即少年英雄甘罗,根据《史记》的记载,甘罗年方十二,就做了秦相吕不韦的家臣,之后为秦使赵,劝说赵王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借以联秦攻燕。赵王依计行事,出兵攻打燕国,“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十几座城池,年仅十二岁的甘罗因此立了大功,被封为秦国的“上卿”(即相国)。甘罗使赵的时间,最早也要到秦王嬴政登基三年以后,最晚也不会超过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的那一年,亦即在前243年—前237年之间。甘罗拜相之后,下落不明,而全国各地则出现了十二处“甘罗墓”,南边一直到江西武宁、江西吉安乃至广西藤县,都有“甘罗墓”的传说。本人曾撰《试论秦相甘罗在赣北等地的遗踪》,认为甘罗受吕不韦的牵连,被迫离开秦国,参与了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行动,故而被迫四处逃亡。甘罗隐居在武宁,表明当时这一带远离战火,比较安全。此外,还有伊叟的传说,这个伊叟隐居在伊山,“伊叟旧宅,县西北三十里伊山之巅,遗址至今存焉。世传秦时有伊叟者,避地于此,织屦置山下,路人以米易屦去,叟徐取米归,不与世接,盖隐君子也。后叟于石湫中拾一卵,五色晶莹,异而伏之,岁余产一龙,腾波而去。”武宁县还有鹭鸶洞,相传秦朝时有罗婆在此安营扎寨:“鹭鸶洞有罗婆寨,四面削立,其上平坦如基,可容千人,至今有瓦砾遗迹,相传秦时罗婆营寨于此。”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大将王翦南征百越之君,《史记·王翦列传》记载:“岁馀,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这时候修河流域的也就被纳入秦国的郡县。艾子国应该被灭,没有单独成为县域,直到西汉建立以后,才被设立为艾县。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文字是石鼓文,因后代出土的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石鼓文发现于唐初,在十个石鼓上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计718字。残存石鼓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宋代郑樵作《石鼓音序》提出石鼓文当为秦刻石,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这一说法基本上可以成为定论。但具体刻于秦朝哪一时期,则有不同说法,多数意见倾向于春秋中晚期或战国前期。 令人惊讶的是,明朝时期武宁县也出土了石鼓文。《道光续修武宁县志》卷十七:“石鼓,在顺义乡三十四都,明时范原泰卜居。雉草荒原,掘井得石鼓,涤之有班,隐隐见蝌蚪文。原泰位之井底,因名其里曰石鼓。嘉靖间,郡庠范瓒淘井出观之,作《石鼓歌》。国朝范伯淳有《后石鼓歌》,并纪其异。”类似记载亦见《同治武宁县志》卷七。明代庠生范瓒《石鼓歌》云:“古有神物名石鼓,碑文字迹半消磨。溯自攻同骋雄骏,纪功勒石辉山河。……我祖卜居欣戾止,凿泉伐出山之阿。太璞天然去雕饰,含章宛尔供摩挲。亦似篆痕久漫灭,浅深隐现如含螺。”诗歌见《道光续修武宁县志》卷四十,亦见《同治武宁县志》卷三十七。据《道光武宁县志》的“疆域图”,顺义乡三十四都位于柳山之南,与传说中为甘罗故居的新华村仅一河之隔。这个石鼓文的拥有者,应该是秦国的一位权贵,显示秦国对武宁已经实行了有效统治(甘罗逃亡之时,应当不会去制作石鼓文)。 周湖岭 两汉三国时期 西汉初年,在江西省设立豫章郡,下辖十八县,其中修河流域有两个县:海昏、艾县。东汉时期,又分出一个建昌县。两汉时期,有关海昏、艾县的记载很少,从侧面反映修河流域还比较安宁,没有较大的动荡。到了东汉后期,出现过一次大的暴乱。据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公元159年)八月,长沙郡、零陵郡聚集了叛贼七八千人,为首者自称“将军”。朝廷派兵讨伐长沙、零陵叛贼时,豫章艾县有600余人应募从军,因没有得到赏钱,遂怀恨在心,发动叛乱,焚烧长沙郡县,进犯益阳,杀了县令,部众越聚越多。朝廷派谒者马睦监督荆州刺史刘度去平叛,又吃了败仗,马睦、刘度落荒而逃。尚书朱穆推举山阳湖陆人度尚任荆州刺史,度尚广招兵马,与部下同甘共苦,发动进攻,把贼兵打得大败,投降的有几万人。此后度尚一路往南进攻,终于平定了这次叛乱。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修河流域突然变得重要起来。有几件大事很值得一提。 (1)孙钟种瓜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至少有六七个地方都有关于孙钟种瓜及安葬其母亲的传说。 赣北武宁县有“孙钟种瓜”传说。《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八:“吴王墓,在武宁县东南八十里吴王峰,相传孙钟葬母于此,其后孙权称吴王,因追称焉。”《嘉靖武宁县志》记载:“今高峰上有古墓迹,俗传疑即其事也。”乾隆二十年《武宁县志》:“县东五十里吴王峰,俗传吴王墓,冶铁成坟,草木不生,即仙人所指葬母处。”明代邑庠汪克淑《续瓜圃说》:“偕友寻源,陟其巅得吴王墓,塘形如铁色,不生茅草,高广约数十步。” 本文来自修水网 根据研究,大约就在党锢之祸的背景下,身为汉阳(甘肃天水)太守的孙耽遭到牵连,全家被流放到豫章郡,孙耽死于永修吴城,孙钟兄弟奉母流落到瓜源,以种瓜卖瓜为生。母亲去世之后,他又迁徙到浙江桐庐,定居在富阳。孙策、孙权开创帝业之后,吴王峰的墓葬得到修缮和祭祀。 (2)西安县的设立 袁术自领扬州牧之后,擅自任命诸葛玄(即诸葛亮的叔父)为豫章太守。朝廷对此不予认可,遂派朱皓为豫章太守。诸葛玄不服,出兵抵抗,朱皓无奈,只好求助于扬州刺史刘繇。其时刘繇的部下笮融已经逃到了豫章郡的彭泽县,刘繇遂令笮融协助朱皓。笮融出兵打败了诸葛玄,诸葛玄败走西城。建安二年(197)正月,百姓起兵造反,杀了诸葛玄。诸葛玄最早建造的“西城”,就是西安县的前身。诸葛玄把这里叫做“豫章郡”,他死之后,刘繇占领了这里,撤掉这个“不合法”的豫章郡,改立“豫章县”,并在北面四十多里处建造了“刘繇城”。建安四年(199)刘繇病卒,他在豫章郡呆了五年,均以“刘繇城”为据点。刘繇病死之后,孙策趁机攻占豫章郡,把“豫章县”改名为“西安县”,又把修河流域分成六个县,西平县、艾县、西安县、建昌县、海昏县、钟陵县。东吴灭亡之后,“西安县”又恢复原名“豫章县”,一直沿用到隋朝统一江南。 本文来自修水网 (3)缭人的出现 在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前,豫章郡建昌县境内出现了一个独立王国,人称“上缭宗民”,其首领称为“宗帅”。《资治通鉴》卷六十二记载孙策派太史慈去察看豫章郡形势,太史慈回来后对他说:“番阳民帅别立宗部,言我已别立郡海昏上缭,不受发召,子鱼但睹视之而已。”“上缭宗民”起源于西汉昌邑王刘贺。元平元年(前74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被立为帝,在位仅27天而被废,仍为昌邑王。元康三年(前63年)又被废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明代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二十:“建昌县有上缭亭,在东南十七里。雷次宗云:亭侧三百家,昌邑王家刘姓,谓之宗人。” 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后汉建安三年,孙策使太史慈觇华歆于豫章,慈还言歆为太守,海昏上缭不受发召,盖是时县民数千家相结聚于上缭,惟刘氏一人为主,谓之宗帅。四年,孙策忌庐江太守刘勋兵强,绐之攻上缭,即此。”“又上缭营,在县南十七里,相传昌邑王贺所筑。今皆为民地。”《建昌乡土志》卷五:“上缭营,东南十七里,在马营区,汉昌邑王所筑,旁有亭。上下居民二百余家,皆刘姓,疑贺所招置。其址今为民地。”综合起来,“上缭营”是海昏侯刘贺建造的城池,因刘姓聚居于此,为汉代宗亲,故称“宗民”,其首领称为“宗帅”。东汉末年,“上缭宗民”拥兵自保,势力很大,一度发展到有一万多家人。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庐江太守刘勋求助于豫章太守华歆,华歆派人去上缭征粮,结果“上缭宗民”拖延甚久,只是打发一点了事,刘勋为此很恼怒。孙策见此情况,便怂恿刘勋去攻打上缭,“上缭宗民”闻讯,坚壁清野,逃之夭夭,刘勋了无所得,反而被孙策抄了老窝。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必然要发兵攻打上缭以征服之,这个豫章郡内的“独立王国”也从此消失了。然而“上缭宗民万余家”的去向却值得人们探究。按《建昌乡土志》卷三: 缭水源出义宁州茅竹山,经新吴由安义流入境,古称上缭水,今有上缭津,即山下渡,为修、缭合流处。……自西南来者为缭水,发源宁州茅竹山,会诸水于靖邑之双溪,又总鹿源巷之泐潭,历安义至闵坊城山间入境,是曰南河。 综合起来,现在流过靖安县城边上的南河,古称“上缭水”,它发源于修水县,往下流经安义县,在永修县境内汇入修河。很显然,“上缭水”应该得名于《三国志》所称的“上缭宗民万余家”。然而孙策所说的“上缭宗民”在今永修县城附近,离靖安县的“上缭水”却比较远。综合起来,孙策在征服“上缭宗民”之后,应当把他们的大部分都迁徙到了大山之中,靖安县一带最多,为此靖安县的河流也就被命名为“上缭水”了。 周湖岭 “上缭宗民”被迁徙到山区之后,在社会状态上实际上还退化了,为此将他们纳入“王化”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南朝陈霸先称帝之后,“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琳”而反叛,这个被称为“洞主”的余孝顷,相当“溪洞之主”,实际上应当就是“上缭宗民”的后代。因为“缭”又写作“僚”“遼”“潦”,所以修河流域带“辽”的地名,多半与“上缭宗民”有关,如“辽山”“辽田”“辽里”“辽东山”,等等。
读吴国富教授《修河流域的早期历史》有感
吴国富教授的《修河流域的早期历史(三国以前)》,原则上不是一篇研究性文章,而是一篇讲座的提纲。今年8月23日下午,我有幸于武宁县太平山佑圣宫,聆听吴教授关于修河流域早期历史文化、太平山文化的讲座,吴教授用的就是这篇提纲。程彦林 吴教授的这篇提纲性文章,以宏大的历史视野,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对修河流域从史前到三国时期的文明演进、族群变迁与政治沿革进行了系统梳理,构建了从尧舜禹时代(距今约4500年前)至三国时期修河流域的完整历史框架。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文章涵盖“阳鸟夷”“三苗”“百濮”“九菌/麇子国”“艾国”“上缭宗民”等关键族群与政治体的兴衰变迁,将夏商周中央王朝的南进、楚吴争霸、秦汉统一等宏观历史进程进行衔接,清晰勾勒出修河流域不仅是本地“三苗—百濮—九菌—艾”文化的摇篮,更是中原王朝经略南方的前沿(禹征三苗、商南征)、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楚文化东进、吴文化西侵)、以及矿产资源(瑞昌铜矿)的战略要地,深刻阐述其连接鄱阳湖平原与赣西北山区、沟通长江与赣江的重要枢纽作用,既填补了赣北早期文明史研究的空白,又是构建“大九江”一体化历史叙事的开创性破题。 文章广泛征引《尚书》《山海经》《左传》《史记》《逸周书》等核心典籍,对“南海”“三危”“黑水”等历史地理概念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考辨(如将“南海”定位于近武汉的云梦泽区域),融入山背文化遗址(修水,新石器晚期)、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武宁出土西周甬钟、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等关键考古发现,为“三苗文化”、“麇子国”、“西周控制”等论点提供实物论证,从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对“靖安”与“靖人/菌人”、“艾人/艾虎”与端午辟邪习俗、“蒲人”与“濮人”、“缭水”与“上缭宗民”等关联进行创新性解读,既是指导如何推进修河、鄱阳湖等赣北古史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又是研究如何构建“大九江”历史文化的方法论。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吴教授在文中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如:将“三苗”南迁的“南海”定位为江汉地区的云梦泽一带,而非现代南海;提出商周时期的“九菌国”可能在靖安一带,并与后来的“麇子国”一脉相承;用靖安李洲坳墓葬的独特葬俗(大规模人殉)反证其墓主非楚国贵族,而可能是“麇子国”君主;将“艾国”之“艾”,从单纯的植物崇拜引申解读为与山地民族(被视为“凶恶”的“艾人”)相关的政治实体。这些新观点视角独特,为破解围绕“大九江”历史文化建设和考古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令人醍醐灌顶,耳目一新。 当然,吴教授此文仅为提纲性质,其中,很多核心论点还需更详实的旁证佐证支撑,很多关键论据还需更直接的考古证据支持,很多精彩论证还需进一步深化。 此文是修河与鄱阳湖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值得高度重视,建议凡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都通读此文,运用好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