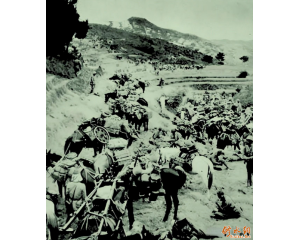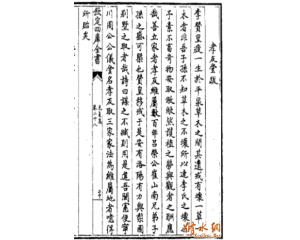|
今年夏秋交替之际,修水县多地又遭遇上连续一个多月高温且少雨的天气,各地都掀起一股抗旱高潮。有颜语“交秋脱伏,晒得肉熟。”所有的庄稼倍受高温煎熬,辣椒、茄子等蔬菜在枝头上就烤干了。 最重要的还是水稻,现在正是孕穗、抽穗的关键时刻。倘若这节骨眼上缺水,那今年的劳作就是白搭,一家人的口粮又得另想办法。  在这条“大动脉”上,还有最值得一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一座座渡槽。在这条水渠上,有不少于六座渡槽,长的达三百多米,最短的也有三十米左右,它们造形各异,尽显智慧的光芒。  湖岭 春水淌过斑驳的槽身,夏风掠过青苔的缝隙,秋阳洒向层叠的石拱,冬雾氤氲沉默的桥墩——四季轮回,渡槽不语,却将一方水土的坚韧与智慧娓娓道来,它是镌刻在田野间的无字丰碑。 在渡槽没有修好之前,家乡的大部分耕地只能种红薯、玉米、荞麦,根本种不了水稻。记得小时候听母亲同我讲过她们用脸盆接水到稻田的故事。 还是大集体年代,我们队上有一片稻田靠当天水的,那年正当水稻孕穗、抽穗时遇上了干旱天气。稻田虽然离小河只有几十米远,但田块却比河道高二十多米,要是在现在这个年代有电、有水泵,这点事根本不算事,可那个时代是一无所有。万般无奈之下,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全队的劳动力不分男女齐上阵,一人一个脸盆,一个挨着一个,从河里取水,硬是把一盆一盆水送到那片田里,保住了那季水稻的收成。 自从家乡的渡槽建好以后,那片水田再也不喊“渴”了。 我第一次见到渡槽的全貌,是六岁那年跟着父亲去小山窝的菜地里锄草,那渡槽就横跨在我家的菜地上。槽身是半圆形的,大约三十米长,两个混凝土立柱支撑着。 父亲同我讲过修建渡槽的事,他也是参与者。渡槽动工那年,全队的劳动力都派去工地上,不论是浇立柱,还是浇槽身,没有一个缺勤的。那时没有起重机,钢筋、混凝土都靠人力抬,浇筑槽身的那天夜里,三盏马灯把工人们的身影投在土坡上,像一群正在搬运山峦的蚂蚁。 本文来自修水网 渡槽通水那天,全队上的人都跑到坡上看。当清清的渠水顺着槽身缓缓流过,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碎银似的光,有人突然哭了起来,接着哭声就像潮水般蔓延开……父亲说那不是伤心,是高兴,是攒了太久的劲终于卸下来了。 在此之前,队里的田地全靠天吃饭,遇上旱年,玉米秆能干得点燃,红薯叶一揉就粉碎。渡槽通水了,几百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第二年夏天,沉甸甸的谷穗把田埂都压弯了。 在众多的渡槽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座特别雄伟的渡槽跨越河道和公路,槽身宽一米七、高六十公分,全长一百五十米左右,十七根双排立柱支撑槽身,最高的一根立柱有三十多米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槽身已出现斑驳锈迹,多处出现漏水、溢水的现象。2016年下半年经过抢救性的修复,那些问题已彻底解决了。 曾经在渡槽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人们,大部分是当地的老农,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他们当中有带着老花镜画图的,有支模的老木匠,有浇混凝土的泥匠,他们不是专家,而是把祖辈传下来的治水经验,一点点融进了钢筋水泥里。渡槽的每个转角留着细微的弧度,那是为了让水流更顺畅;槽身两侧特意砌了排水孔,防备暴雨时水位过高,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都是工人们在工棚的油灯下,反复推演出来的。 周湖岭 在我家乡,还有一座包含艺术与科学结晶的渡槽。它分上下两层,上层通水,下层供人通行,设计巧妙,不仅灌溉着大片农田,还方便了村民过河赶集,是重要的水利工程和充满温情的记忆载体。 渡槽就像一位忠诚的守护者,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实地履行着疏浚水流、浇灌沃野的职责,让一方土地充满生机与活力 。 “水流过的地方,就会留下痕迹。”那些流过渡槽的水,灌溉了无数庄稼,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而这座渡槽,早已不是冰冷的建筑,它是家乡的血脉,是刻在土地上的史诗,是那些平凡的人们,留给大地最温暖的印记。 |